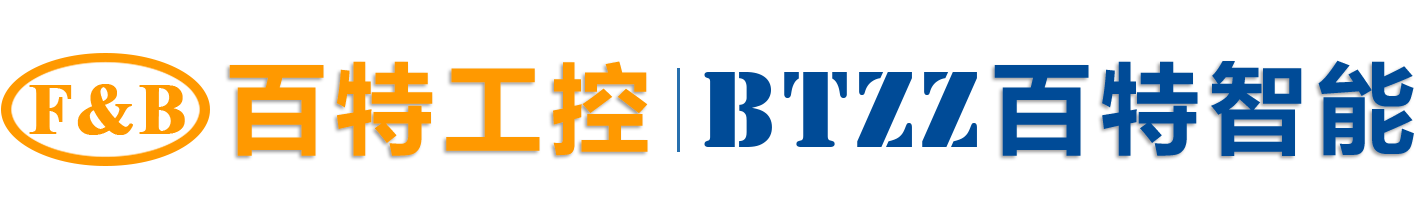“共享”賦能“制造” 不隻是讓閑置設備忙起來
發展共享制造,既可以讓掌握制造資源的龍頭企業搭建平台,将制造能力分享出去,以大帶小,找到一種新的盈利模式,也可以促進制造業專業化分工,讓企業集中精力發展核心能力。
提到共享經濟,人們很容易想到“Uber租車”——利用移動設備、評價系統、支付、LBS等技術手段有效地将汽車需求方和供給方進行最優匹配,達到雙方收益的最大化。
近年來,基于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的崛起,這種共享經濟也開始從消費領域向生産制造領域加速滲透,許多工廠開啓了“共享制造”模式,制造業未來将成爲共享經濟的“主戰場”。
10月29日,“共享制造”迎來政策利好——工信部發布《關于加快培育共享制造新模式新業态 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提出,到2022年,形成20家創新能力強、行業影響大的共享制造示範平台;推動支持50項發展前景好、帶動作用強的共享制造示範項目;到2025年,共享制造發展邁上新台階。
讓企業換個玩法更好活下去
“共享制造就是共享經濟的創新模式在制造業的應用。比如,很多小企業買不起大企業的高價值生産設備,在設備空閑時,大企業将這些設備開放給小企業使用,就是一種制造能力的共享。”浪潮集團執行總裁王興山對科技日報記者說,“但是,共享制造遠不止于此,創新能力和服務能力也在共享制造的範疇内。從虛拟領域向實體領域延伸拓展,在研發設計、加工制造、生産服務等各環節,共享經濟對制造業生産組織方式産生着深刻影響。”
王興山的觀點和工信部相關負責人不謀而合。據該負責人介紹,共享制造的内容其一便是制造能力共享,主要包括生産設備、專用工具、生産線等制造資源的共享;其二是創新能力共享,主要包括産品設計與開發能力等智力資源共享,以及科研儀器設備與實驗能力共享等;其三是服務能力共享,主要圍繞物流倉儲、産品檢測、設備維護、驗貨驗廠、供應鏈管理、數據存儲與分析等企業普遍存在的共性服務需求的共享。
王興山舉例說:“比如工業互聯網領域的開源,這就是一種創新能力的共享。從2010年開始,國内機構就在探索将雲計算的理念帶入到制造業,也就是雲制造的模式,提出了‘分散資源集中使用,集中資源分散服務’的理念,這是一種制造服務化的思維。”
共享制造不僅在國外已有成熟的應用案例,在國内也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發展基礎。如機械加工、電子制造、紡織服裝、科研儀器、工業設計、檢驗檢測、物流倉儲等領域,已經有一批典型的共享制造平台,形成了産能對接、協同生産、共享工廠等多種新模式新業态,顯示出很大的發展活力和潛力。
在王興山看來,推進共享制造的目的,正是爲了全社會制造資源的集約化配置,從總體上減少重複投入、解決局部資源短缺問題、提高創新能力。
工信部相關負責人指出,對于制造企業自身而言,發展共享制造,既可以讓掌握制造資源的龍頭企業搭建平台,分享制造能力,以大帶小,找到新的盈利模式,也可以促進制造業專業化分工,讓企業集中精力發展主業,提升核心能力。這将有利于提高産業組織柔性和靈活性,推動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促進産品制造向服務延伸,提升産業鏈水平,加快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有利于降低中小企業生産與交易成本,促進中小企業專業化、标準化和品質化發展,提升企業競争力,對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融合發展、培育壯大新動能、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在深圳寶安區燕羅街道就有這樣一家“共享工廠”,從大型設備到工人,從創意到品牌,一切都可以共享。眼下,這裏已經彙聚了數十家企業、團隊和數百位“創客”。在共享制造的模式下,他們“抱團取暖”,共同度過小微制造業的“陣痛期”。廠房、設備、工人、訂單、财務與行政人員都是共享的,數十個企業和團隊共享一個财務辦公室,省去了單獨雇傭的人力費用。
“共享制造孕育着未來社會生産分工形态的巨大變革。”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新紅說,“在這一模式下,企業可以換個玩法更好活下去。”
共享制造還需進一步完善生态
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報告顯示,2016至2018年我國制造業産能共享市場規模分别約爲3300億元、4120億元和8236億元,年增速從約25%提高到約98%。2018年産能共享市場交易額占我國共享經濟市場總規模的比重從上年的20.1%上升到28%,提高了近8個百分點。
工業和信息化部産業政策司相關負責人稱,我國在機械加工、電子制造、紡織服裝、科研儀器、工業設計、檢驗檢測、物流倉儲等領域湧現出一批典型共享制造平台,形成了産能對接、協同生産、共享工廠等多種新模式新業态,顯示出很大的發展活力和潛力。
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雖然是制造業第一大國,但産業大而不強、結構不合理、創新能力弱、資源利用效率低。我國共享制造總體仍處于起步階段,依然面臨共享意願不足、發展生态不完善、數字化基礎較薄弱等問題。”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長餘曉晖說。
當前,許多擁有閑置生産資源或科研儀器設備的企事業單位由于體制機制原因,并不願意向中小企業開放共享。傳統制造模式下,已經形成了以實體工廠爲核心的标準信任體系,而共享制造模式由于具有多主體協同、虛拟化制造等特點,在信用評價、産品标準、生産規範等方面還很不完善。
與此同時,相當一部分企業和部門對制造業産能共享的認識不足,部分企業對産能共享理解不到位,往往将互聯網平台看作簡單的交易平台,導緻企業參與産能共享的内生動力不足。
對此餘曉晖表示:“完善發展生态是提升社會對共享制造新模式認知度的關鍵環節。要從創新資源共享機制、推動信用體系建設、優化完善标準體系三項任務入手,進一步完善共享制造發展生态。”
“當前,政府和社會正推動大企業‘搭平台、建生态’,中小企業‘上平台、進生态’。随着共享制造的發展,‘平台+生态’将成爲制造業主要的商業模式和産業變革潮流。”王興山說。
從4方面發力迎發展窗口期
“我國制造業門類齊全,細分行業衆多,到2022年打造20家共享制造示範平台、50項示範項目的目标樂觀可行。”在王興山看來,經過多年探索,我國已經有發展共享制造的産業基礎,依托于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5G技術的日益成熟,共享制造正迎來發展窗口期。眼下,我國全産業鏈資源共享亦向着“業業有平台”的方向努力。
如何完成這兩個目标呢?工信部已從平台、集群、生态和基礎4個方面給出了非常明确的重點任務:一是培育共享制造平台,積極推進平台建設、鼓勵平台創新應用、推動平台演進升級;二是依托産業集群發展共享制造,探索建設共享工廠、支持發展公共技術中心、積極推動服務能力共享;三是完善共享制造發展生态,創新資源共享機制、推動信用體系建設、優化完善标準體系;四是夯實共享制造發展的數字化基礎,提升企業數字化水平、推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強化網絡安全保障。
此外,支持和引導共享制造健康發展的頂層設計,對培育壯大新動能、實現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亦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
正如美國著名雜志《連線》的創始主編凱文·凱利所說:“任何可以被共享的都能以上百萬種我們今天尚未實現的方式,被更好、更快、更便利、更長久地共享。”當共享的觸角碰到産業上遊時,融入“共享制造圈”的企業将會有更廣闊的發展前景。